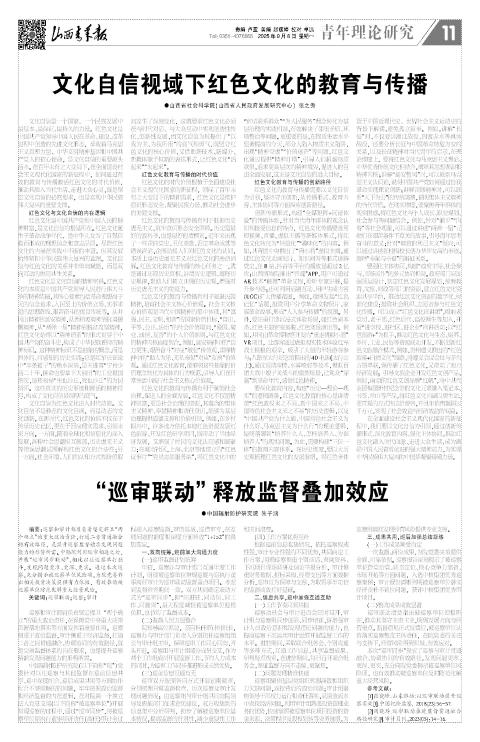文化自信视域下红色文化的教育与传播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张之秀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先进文化形态,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中华文明精神基因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活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如何通过有效的教育与传播激活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其融入当代生活、走进大众心灵,既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红色文化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是中华儿女为了自强自救而形成的理想信念和意志品质。尽管红色文化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的丰富,但其发展始终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文化自信与红色文化的关系并非单向赋能,而是双向互动的协同共生关系。
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精神密码。红色文化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精神结晶,其核心要素包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追求、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等。从井冈山精神到延安精神,从西柏坡精神到抗美援朝精神,从“两弹一星”精神到脱贫攻坚精神,红色文化始终以“精神谱系”的形式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种精神标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可感知的历史实践:它是红军长征途中“半条被子”的鱼水深情,是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工业报国热忱,是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为民情怀。这些真实的历史事迹和鲜活的精神符号,构成了文化自信最深厚的底气。
文化自信为红色文化注入时代动能。文化自信不是静态的文化自满,而是动态的文化创新。在新时代,红色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承历史记忆,更在于回应现实需求、引领未来方向。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试图解构红色文化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人们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要求红色文化必须在与时代对话、与大众互动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文化自信为其提供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底气和勇气,既坚守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又借助新技术、新媒介、新载体赋予其新的表达形式,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火起来”。
红色文化教育与传播的时代价值
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根植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回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精神需求,红色文化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凝聚民族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支撑。
红色文化的教育与传播有利于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歪曲党史、丑化英雄、否定革命成就等错误言论,企图动摇人们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本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对红色文化的恶意消解。红色文化教育与传播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通过还原历史真相、讲清历史逻辑、阐释历史规律,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免疫力。
红色文化的教育与传播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准则,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例如,延安精神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对应“敬业”价值观,雷锋精神中的“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对应“友善”价值观。通过红色文化教育,能够将这些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红色文化的教育与传播有利于赋能社会治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不仅是精神财富,更是社会治理的资源,其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和责任意识,能够为基层治理提供道德支撑和价值引领。例如,在乡村振兴中,许多地方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开发红色研学项目,既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又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在城市社区,上海、北京等地建立的“红色议事厅”“党员志愿服务站”,将红色文化中的“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理念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践机制,有效解决了邻里矛盾、环境整治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今天,部分人陷入物质主义陷阱,出现“精神空虚”“价值迷茫”等问题,红色文化通过提供“精神灯塔”,引导人们超越物质欲望,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正是文化自信的远大目标。
红色文化教育与传播的创新路径
红色文化的教育与传播需要以文化自信为引领,坚持守正创新,从传播形式、教育内容、主体协同等方面探索创新路径。
创新传播形式,构建“全媒矩阵+沉浸体验”的传播体系。针对当代青年群体的观念认知和接受信息的特点,红色文化传播要善用短视频、直播、虚拟主播等新媒体形式,将红色文化转化为“轻量化”“趣味化”的内容。例如,共青团中央推出了“青小豹”虚拟主播,通过红色文化动画短片、知识问答等形式讲解党史,在B站、抖音等平台的播放量超过2亿次;山西博物院推出“晋魂”APP,用户可通过AR技术“触摸”革命文物,聆听专家讲解,提升参与感;还可利用话题互动、用户生成内容(UGC)扩大传播范围。例如,微博发起“红色记忆”话题,鼓励用户分享革命文物照片、家族革命故事,形成“人人参与传播”的氛围。另外,要注重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如红色剧本杀、红色主题密室逃脱、红色实景演出等。例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开发的“重走挑粮小道”VR项目,让游客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红军战士挑粮的艰辛,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游客参与;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推出的4D电影《太行山上》,通过震动座椅、水雾喷射等技术,模拟百团大战中娘子关战斗的激烈场景,让观众“穿越”到革命年代,感悟红色精神。
要深化教育内容,构建“历史—理论—现实”的逻辑链条。红色文化教育的核心是讲清楚“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的历史逻辑,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理论逻辑,最终落脚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现实问题。为此,需要构建“三位一体”的教育内容体系。在历史维度,要以大历史观梳理红色文化的发展脉络,将红色事件置于中国近现代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背景下解读,避免孤立叙事。例如,讲解“长征”时,不仅要讲湘江战役、四渡赤水等具体战役,还要分析长征与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系,以及长征精神对当代青年的启示,在理论维度上,要将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阐释其思想渊源和精神内核;讲解“延安整风”时,可以联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说明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自我革命实现理论创新;讲解雷锋精神时,可以联系“天下为公”的传统美德,说明集体主义精神的当代价值。在现实维度,要聚焦青年群体的现实困惑,将红色文化与个人成长、职业规划、社会参与等问题结合。例如,针对“躺平”“内卷”等社会现象,可以通过讲述“两弹一星”元勋们在艰苦条件下攻关的故事,引导青年思考奋斗的意义;针对“精致的利己主义”倾向,可以通过讲述张桂梅校长创办华坪女高的事迹,阐释“奉献与幸福”的辩证关系。
要强化主体协同,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协同机制。政府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红色文化发展规划,统筹教育、文旅、财政等部门的资源,建立红色文化资源共享平台,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标准化建设;鼓励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红色文化传播。可以成立“红色文化宣讲团”,吸纳老党员、老干部、红色后代、高校师生等加入,开展“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宣讲活动;以“红色旅游+”为抓手,推动红色文化与生态、康养、乡村、工业、民俗等资源联动开发,不断创新红色文旅融合模式,例如,贵州遵义推出的“红色旅游+白酒文化”线路,将遵义会议会址与茅台古镇串联,既传播了红色文化,又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引导文旅企业开发红色文创产品,例如,南京的红色文创品牌“红帆”,将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的文化元素融入笔记本、书签、丝巾等产品,将红色文化内涵以更生动、更直观的方式传达给游客,并且年销售额超过千万元,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要以文化自信为引领,通过创新传播形式、深化教育内容、强化主体协同,推动红色文化融入时代血脉、走进大众生活,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