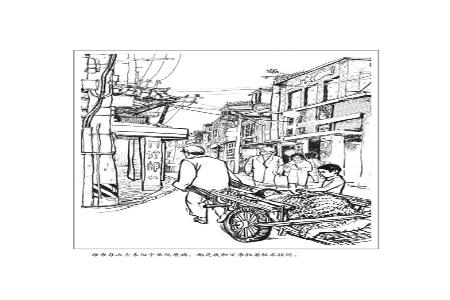春蚕到死丝方尽
韩国华(1924—2016)山西襄垣人。1941年参加工作,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至1951年7月,分别在长治华丰铁厂、长治军工二分厂任材料收发、保管;1951年 8月至1954年12月,先后任长治三〇四厂公安科内勤、保卫科副科长;1955年1月至1957年5月,任山西省公安厅第七处副科长;1957年6月至1959年5月,任华北煤田地质勘测局一一九队保卫科科长;1959年6月至1960年6月,任阳泉矿务局地质处副处长;1960年6月至1962年5月,任阳泉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1969年,任湖南湘勘一队党委书记;1979年,任煤炭部地质总局干部学校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
讲述人:韩太生 讲述时间:2022年8月20日 整理人:江雪
在抗日烽火中历练成长
1924年农历正月十一,我父亲韩国华(也叫韩金鑛)出生在襄垣县王桥镇返底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我爷爷韩春景去世,当时我姑姑九岁,大伯六岁,父亲只有三岁。
听父亲说,1938年4月,日本鬼子从潞城牛王岭下来,第一次到襄垣县返底村“扫荡”。因为返底村附近的黄碾、小河堡、东周都有日军的炮楼,日本鬼子到黄崖洞“扫荡”也经常路过返底村,我奶奶经常带着大伯、姑姑和父亲“躲反”,他们在山上废弃的土窑洞里一躲就是好几天。
1941年,八路军工作团秘密来到返底村,当时,共产党的区政府就驻在村里,区公安助理叫解希荣。他看我父亲机灵且靠得住,就经常派我父亲往敌占区襄垣县关道村送信。父亲把情报交给南里信的通信员,再由南里信通信员把情报送到襄垣城里。这时候,父亲已经成为一名地下通信员。百团大战打响后,父亲经常跟着八路军游击队参加破坏鬼子的公路、铁路行动。1942年8月,十八岁的父亲在区政委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父亲担任了村里的公安员。1944年,年仅二十岁但已被革命历练出来的父亲担任了返底村副村长,一直到1946年5月。
父亲担任副村长期间做了很多抗日革命工作,也参加过一些战斗,比如解放河南新乡的战斗。但父亲的主要工作是动员村民参军,组织人员运送伤员、物资,发动村民为八路军做军鞋,支援前线,破坏鬼子的铁路,抬铁轨,支援八路军工厂用料等。听父亲说,有一次,区里组织民兵夜里到五阳矿破坏鬼子的铁路,被日本鬼子发现了,鬼子立即向他们追来。父亲他们人少,不敢硬拼,只好赶紧撤退。好在大家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三绕两绕,都跑了回来,有惊无险。
我父亲的堂哥韩有其,我叫他六爹,就是我父亲动员去参的军。我六爹参加过很多次战役,比如上党战役、挺进大别山,获得过很多战斗英雄奖章、奖牌。
服从组织安排,做一块有用的“砖”
抗战胜利后,位于黎城黄崖洞的兵工厂迁移到了长治潞州区塔岭山下的南石槽村。当时,解放战争刚拉开序幕,战场上急需各种武器。1946年6月,我父亲被调到华丰铁厂 (后移交长治兵工厂一分厂,即淮海工业集团)。后来,父亲又经历了几次调动。1955年1月,被调到山西省公安厅七处,担任副科长。我就是父亲在太原工作时出生的,所以我的名字叫“韩太生”。1957年7月,公安厅七处被撤销;8月,父亲被调到了华北煤炭地质勘探处,担任保卫处秘书科长。因为父亲喜欢跑野外,1957年6月,又被调到了华北煤田地质勘探局一一九队保卫科,担任科长。那两年,父亲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父亲的努力下,1959年一一九队保卫科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9月,父亲参加了全国公检法政治先进代表大会,还获得了一枚奖章。
1959年6月,父亲被调至阳泉矿务局地质勘探一一九队担任副队长;1962年6月,父亲被调至山西省煤炭管理局地质勘探局一一九队任副队长;1964年,父亲又被调到山西长治一一四地质勘探队任队长兼党委书记。当时一一四地质队驻地在高平赵庄煤矿附近,是一个亏损单位。父亲到一一四地质队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让地质队扭亏为盈。1966年2月16日,父亲参加了全国基本建设大会,一一四队因为扭亏为盈成为典型,受到大会的表彰。在这次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了全体代表,并与代表们合影留念。父亲把那张照片装裱起来,一直挂在家里很多年。
1966年,毛主席提出要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父亲所在的一一四地质队按照上级要求,需到南方勘探新的煤炭资源。一一四地质队职工大多是北方人,不愿意到南方去。但父亲党性原则很强,认为革命工作就是党要求到哪里就到哪里,便带队去了江西;过了半年,一一四地质队又整队到了湖南。
1969年,我父亲离开一一四地质队,调至湖南湘勘一队,担任党委书记。湖南湘勘一队在父亲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都非常出色,1978年2月被煤炭部和湖南省命名为“大庆式企业”。父亲参加了全国“学大庆、赶开滦”群英大会,受到首长的接见,获得了煤炭部功勋奖、湖南省先进标兵等很多荣誉。当时,获煤炭部功勋奖的,全国只有十个。几年后,父亲被调到煤炭部一七三地质队,担任书记;1979年,又被调到位于河北涿州市的煤炭部地质总局干部学校,担任党委书记。
父亲是1984年离休的,因为老家在长治襄垣县,落叶归根,异地安置在长治市一一四地质队家属院。父亲就在这里一直住到他去世。父亲这个家虽然简陋,但父亲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安稳的一段时期。
地质队主要搞勘探工作,说通俗一点儿,就是找矿。父亲一生如浮萍漂泊,哪里有矿就到哪里;又如一块砖,祖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他从没有叫过苦,也从没有埋怨过。
无私奉献 甘为他人照前路
我父亲为国家奉献了一生,却被我母亲埋怨了一生。
父亲在长治兵工厂时,与同是返底村老乡的母亲结了婚。当时,厂里没有房子,他们借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我母亲一共生养了三个孩子,我上边原来有一个哥哥。当时父亲每天忙于工厂的工作,根本顾不上家里的事情。我哥那会儿只有几个月大,一次感冒发烧,母亲叫父亲找医生。父亲到医院找了医生,告知医生地址后就着着急急地去了厂里。母亲在家里急得团团转,再加上没有经验,等医生来了,哥哥已经不行了。
我下面还有过一个弟弟,也没有活下来。当时父亲在一一九地质队工作,队部家属区离阳泉市里比较远,从队部到市里医院走近路要翻过一座山。那年,弟弟生病住院,治疗得差不多了,准备出院。母亲对父亲说,你跟队上要辆车接孩子出院吧。父亲那会儿是副队长,地质队也有车,但父亲坚决不同意。我弟弟胖,父亲用小被子包着刚出院的弟弟爬山路,不一会儿便走出了一身汗。天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包弟弟的小被子掉了,匆忙赶路的父亲却没发现。那天晚上,弟弟因为吹了山风而复感,高烧不止,没来得及送医院就没了。
1975年到1977年间,住在湖南的母亲因为不适应当地气候,经常生病。每次去耒阳中医院看病,都是我和父亲拉着板车接送。耒阳中医院距我们住的地方有七八里路,而湖南湘勘一队有两辆吉普车,我那时已参加了工作,就在队里开车,但父亲从没跟队里要过车,也不允许我开队里的车送母亲去看病。严以律己,对于父亲来说绝不是一句空话。公家的便宜再小,父亲也不占;但单位同事的事再小,他也会想办法去解决。父亲担任湘勘探一队党委书记期间,非常关心职工群众的生活。当时队里有一部分职工家属虽有城市户口,却没有工作,家里孩子多的,经济自然就紧张。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想方设法建了一个五七工厂,从修配厂抽调一部分技术工人过去,然后将很多没有工作的家属安排进厂上班。五七工厂主要负责修理旧钻头和钻具,废物利用。厂里买来建桥工地的废旧钢筋,加工成钢粒。钻头打钻时,把钢粒撒进去,钢粒有棱角,可以增加钻头与石头的摩擦力,提高钻探效率。
还有一部分职工家属在农村老家生活,职工们想家,难以安心工作。父亲就设法筹集资金,在附近农村买了几座山、一些田地,还有水塘,让这些家属迁过来,种田、养鱼、种茶油树、养家禽,一举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职工情绪稳定了,工作积极性也提高了。
父亲总想着工作,想着同事,唯独想不到自己。我母亲跟着父亲“南征北战”,居无定所,吃了一辈子苦,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到老,连养老金都没有。
因为父亲工作上的 “颠沛流离”,我也只能跟着“漂泊不定”。我在山西阳泉一一九地质队子弟学校上过学,在高平县赵庄村学校上过学;十二岁时,我跟随父亲到了湖南怀化,在怀化芦阳镇小学上学。1974年,我在湖南参加工作,开汽车,很辛苦。当时队里有很多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父亲却从来没有想起过我。
终身学习吐尽最后一口“丝”
2016年4月2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他写下的三十五页共十万多字的 《返底村村史》手稿。因为我在涿州上班,而父亲在长治生活,父亲什么时候有了写村史这个想法,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写了多久,改了多少遍,我不得而知。留下来的两本手稿,第一本封面上写着四个字“想写村史”。看着这几个字,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无法想象,是什么支撑九十岁的父亲完成这样庞大的写作计划的,他又是怎样趴在桌上一字一句写的。这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缕丝”,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片爱。
村史手稿一共两本,第一本有少许地方进行了修改批注;第二本大概是父亲誊写下来的,非常整齐。遗憾的是,这一稿只誊写到了第十页——父亲没有来得及完成就离开了……
我细细翻看了父亲写下的村史,尽管我是外行,也忍不住为父亲的认真、仔细而心生敬畏。整本村史内容详细,结构安排得当,对于研究返底村的历史很有价值。
父亲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学习。小时候家里穷,父亲只上过两年冬学。他所掌握的知识,全靠自学。父亲喜欢写日记、做笔记,留下了厚厚的一摞笔记本。父亲的笔记本中,还有几个摘抄本,其中一本,是父亲抄写的关于老一辈革命家 “家规家风”或者廉洁自律的文章,如《贺龙同志同群众共甘苦》《毛泽东同志的两封信》《周恩来的十条家规》《刘少奇同志的 “四不准”》《陈毅与亲属》《任弼时“三怕”可做座右铭》《彭德怀——招待的电影我不看》等等,父亲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抄到90年代。
读父亲的摘抄本,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以前我很不理解的父亲的一些做法,现在我在这个摘抄本中找到了答案。
一篇关于贺龙的文章,大意是这样的:贺龙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把儿子送到农村参加劳动。儿子第一次回家,贺龙摸摸他的手掌,说,手光光的,还不行。儿子只好继续下乡劳动,直到手上磨出一层老茧……我一直想上大学,但父亲却让我开汽车、当司机,做了一辈子基层工作。联想到贺龙对儿子的教诲,我明白了父亲——国家领导人克己奉公的做法早已为他树立了榜样。
(下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