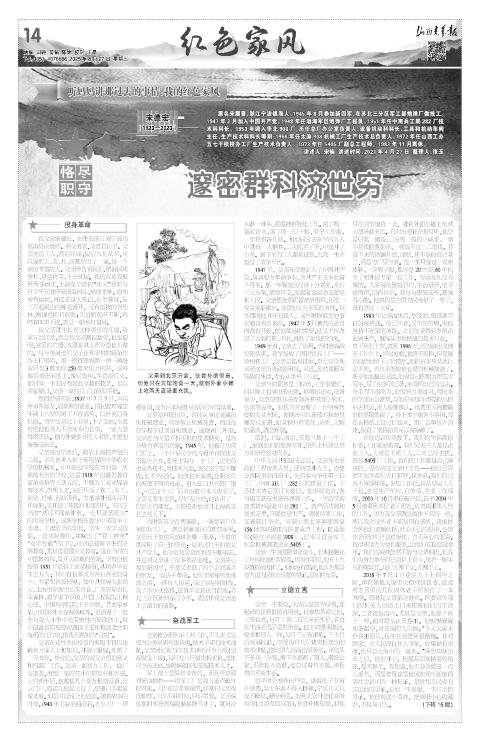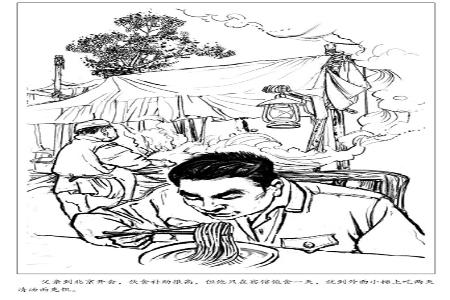邃密群科济世穷
宋德宏(1923—2023)原名宋赓赉,浙江宁波镇海人。1945年8月参加新四军,在苏北三分区军工部炮弹厂做技工。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渤海军区炮弹厂工程员。1951年任中南兵工局282厂技术科科长。1953年调入华北908厂,历任总厂办公室负责人、设备机动科科长、工具和机动车间主任、生产技术科科长等职;1966年任太原908机械工厂生产技术总负责人。1972年任山西工办五七干校校办工厂生产技术负责人。1973年任5405厂副总工程师。1983年11月离休。
讲述人:宋楠 讲述时间:2023年4月27日 整理人:张玉
投身革命
我父亲宋德宏,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前袁村。祖父务农,父亲是长子。父亲先是工人,然后经商,最后入伍从军,可以说把工、农、兵、商都经历了一遍,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父亲曾告诉我们,镇海民风淳朴,景色优美,十分宜居。我的故乡双板桥西邻甬江,上海至宁波的“江天”客轮每日下午五时停靠镇海码头,热闹非常。南侧旁有运河,再过去是大陈山,长年葱绿,从三月起满山的鲜花盛开,还有挺拔的青松林、嫩绿色的苜蓿地;儿童嬉戏声不断,鸡鸣狗叫声不绝,真是一幅乡村美景。
我父亲就生长在这样美丽的江南,我家五世同堂,祖父和父亲都很勤劳,也很聪明,家里的竹器、木器家具大部分是他们做的。每年冬闲他们父子还到邻村的锡箔作坊去打锡箔,用一把铁锤将锡一锤一锤敲成只有3微米厚250毫米见方的箔,这种锡箔焗在麻纸上,做冥钱用,生意很红火。那时候一个农民有如此卓越的技艺,足以养家糊口,父亲一家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局势骤变紧张。国民政府规定年满十六岁的男丁不准离乡,以补充后备兵源。当年父亲已十五岁,个子又高,乡政府把他也列入不准离乡的名单,一家人急得团团转。他的外婆多方托人求情,才把他偷偷送出去。
父亲逃出宁波后,跑到上海投奔他的二叔。不久他考入位于英租界的中华职业学校机械系。中华职业学校在当时是一所鼎鼎有名的学校,它是1918年由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等人创立的,主要为工商业界培养技术、管理人才,先后开设了铁工、木工、商业、机械、石油等科。为抵制外国商品对华倾销,又开设了电镀科和纽扣科。不同于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学校,这所学校在教学中采取半工半读、工读结合的学制,学生一边学习技能,一边实际操作,并喊出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的口号,同时还强调学生的品格教育,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这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是开天辟地的创新。学校自建校至1951年底轻工业部接管,共培养毕业生近万人;其中有很多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专家和各级领导,如中共领导人张闻天、上海市原副市长朱宗葆、广东省原省长朱森林、数学家华罗庚、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心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世绩、艺术家秦怡、中国驻外大使祝幼琬等。更涌现了一批在与敌人斗争中光荣栖性的革命烈士,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曾就读于重庆校区会计训练班的江竹筠,即我们熟知的“江姐”。
父亲在这些杰出校友的熏陶下得以接触多方面人士和知识,开阔了眼界,练就了一身本领。毕业后,父亲的叔父介绍他到义和机器厂工作。父亲一面努力工作,一面广交朋友,得到厂里的先生们的信任和好感。大约两年后,他邀集几个朋友租借设备,自立门户,揽活儿做起大包工,想要白手起家做老板。但是时局没让他如愿。随着战事的升级,1943年上海全面沦陷,大小工厂一律被征用,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后方军需基地。
父亲是科班出身,曾经从事过金属冶炼和锻造业,特别擅长机械制造,而且他在学校学过英语和俄语,通晓两门外语。父亲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技术精英,是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1945年,他被日伪部门盯上,一个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找我父亲提出合作,要在上海办一个工厂,让他负责业务技术,用技术入股。我父亲宁愿不赚钱,也不当汉奸。他改名宋多鸿,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悄悄逃走,进入虹口万兴铁厂做工,可是这个工厂后来也被日本人收买了,父亲又萌生去意。经好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姓王的朋友,王伯伯劝他离开上海到苏北去闯天下。
当时到苏北有两条路,一条是到日伪军的兵工厂,一条是到解放区的新四军里。父亲问王伯伯究竟该走哪一条路,王伯伯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原来这位王伯伯是共产党人。他介绍我父亲到新四军那里去,并且对父亲讲了很多革命道理。父亲决心参加新四军,于是又串联了四个志同道合的密友,一起去干革命。他们非常秘密地逃离上海,一路有人接应,闯过层层封锁线,花了不少买路钱,总算平安到达目的地:苏北三分区新四军司令部。就这样我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奋战军工
父亲被分配到军工科工作,不久正式定级为公务员副科级待遇。技术干部有技术津贴,父亲回忆他当时技术津贴评为八级(最高级是十级),每月发八斤猪肉折实价,这比司令员还高,说明解放区很重视技术人才。
军工战士是异常辛苦的,而且经常面对流血牺牲——因军工厂是敌人重点破坏的对象。工作更是非常艰苦,经常白天黑夜连轴转,工作不讲时间,只讲需要。父亲说他那时实在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就用冷水淋一淋头,提提神再继续工作。渴了喝一茶缸冷水,饿了吃一口干粮,至于工作服,一年难得洗几回。和他同时去参军的五人中就有一人牺牲,二人吃不了苦,中途开了小差。留下来的二人都负过伤,九死一生才挺过了战争年代。
1947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誓言要为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那一年解放区经济十分紧张,实行三大方案,紧缩开支,发起献金运动支援党和人民。父亲把全部积蓄献给组织,还把一枚金戒指献出。这是他大公无私的表现。其实那时他并非有钱人,这些财物都是他节衣缩食省出来的。1947年5月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开始,依据战场的需要,他又主持改进了火炮的曲、平射,得到了前线的好评。
1949年春,父亲去了徐州。当时淮海战役刚结束,我军接收了国民党兵工厂——徐州铁工厂,父亲是高级技师,责无旁贷地来到这里负责武器研制。从此,他结束随军转战的生活,专心从事军工行业。
父亲当时职务是工程员,工作很繁忙,而且晚上有事也要出勤。环境很恶劣,设备很少,父亲总想办法改制各种铣床、车床、钻床等设备。他说当时他做了一台特殊角度的尖头车床,使铁屑可以连续不断地呈螺旋状前进,如果钢材有夹灰、杂质、大颗粒晶体,就会断裂。
那时,上海、南京、无锡三地十一个工厂,承制他们的炮弹零件,组织上任我父亲为质量检验总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作为革命的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党外人士,为建设国防事业而奋斗,先后参与华东第三兵工厂、中南331厂、282厂的建设工作。中苏技术协定签订失败后,他奉调北京,参与俄文新技术资料译制工作。一年后带新技术资料派赴中南282厂,搞产品试制和技术定型,开展批量生产。刚刚结束工作,又被调往华北,来到山西太原筹建国家156项苏联援建的国家重点工程:防毒器材(防化学武器)908厂,后来又建设军工配套机械制造企业5405厂。
父亲一生为国防事业奋斗,长期接触化工材料使他积劳成疾。因身体原因,他五十九岁就提前离休了。但他没有怨言,他认为那是他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见证,是他的光荣。
立德立言
父亲一生勤俭,生活以温饱为原则,连起码的花费都能省则省。他参加革命之初,工资很高,每月工资二石大米折实价,衣食住生活必需品是供给制。他主动要求取消,要求和别人一样,每月三元钱津贴。三个月后领导批准,享受每月八斤猪肉折实价的技术津贴,这比别人仍高出很多倍。可他从不多花一分钱,攒下来都帮了别人、捐给公家,不管收入高低,他总过着布衣暖、菜根香的平淡生活。
他平时公差外出开会,饿着肚子节省补助费,坐火车舍不得买卧铺,宁愿几天几夜不睡觉,硬座到底。他到北京开会住高级宾馆(北京友谊宾馆),伙食补助很高,但他只在宾馆饱食一天,就到外面小摊上吃两天清汤面充饥。有时出差住在招待所,他总是只吃一碗饭、二分钱一碟的小咸菜、一碗不花钱的葱花汤,一顿饭不过一二角钱。节省下来的高额补助、津贴,并不是他自己拿了,而是为厂里节省。他一生只穿过一双新皮鞋、一身呢子服,那还是20世纪60年代为了和外国专家一起工作,为顾及礼仪而做的。人家说他勤俭节约、生活艰苦,他不觉得苦,自得其乐。我每每想到这些,都觉得心酸。他真的是为国为民奉献了一辈子,没有享过一天福。
1983年父亲离休后,享受地、师级副厅(局)级待遇。他已年老,又带伤带病,但他坚持不在家吃闲饭。之后他受聘到乡镇企业搞生产,继续从事他精通的技术行业,一直干到七十岁,直到1996年,因为脑出血倒在工作台上。经过抢救,他终于脱险,但是脑出血给他留下了后遗症,他的右半身从此行动不便,再也不能做他心爱的机械制造了。所幸他头脑还灵活,他靠自己的毅力用左手写字,写了很多回忆录,来缅怀自己的过去。左手写字很吃力,他很努力地练习,写出来的字迹还是潦草,与他原来那手漂亮的小楷相去甚远,别人很难辨认。他就更不肯糟蹋好的笔墨纸砚了,连个本子都舍不得用,写在表格纸上自己订起来,用广告单包个封皮,我看了觉得简直可以说寒碜了。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的生活都很朴素,工作都很勤奋。我们兄弟三人都是企业工人,大哥是下岗工人,二哥已经去世,我在5405厂工作。我们的工作都是自己解决的,没有沾过父亲什么光——他自己固然不愿为我们去打招呼,找关系;我们自己也不屑那样做。参加工作后,我从基层工人干起,去过生产车间、宣传部、党委工作部等。2003年10月单位破产后,我于2004年5月被调到单位老干部处,负责离退休人员的工作。因为我父亲就是离休干部的一员,所以我对这些老干部特别有感情,我能体会到他们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想法,也能体会到他们日益边缘化、力不从心的悲哀。我尽职尽力为他们服务,让他们安稳度过余年。我们的成绩虽然不能与父辈相比,但我们也努力地在自己岗位上奋斗,做好一颗平凡的螺丝钉,我们无愧于父,无愧于心。
2018年7月1日建党九十七周年之际,单位属地太原市尖草坪区区委、区政府为区里的几位离休老干部制作了一本画册。那时我父母都还健在。区委宣传部门的相关人员还上门来拍摄他们的生活照,二老都很高兴。尤其是父亲,他像个孩子一样,面对镜头认真摆拍。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对在场的人们说:“今天大家来给我拍照片,我实在感觉到很惭愧。我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什么贡献,如果说有贡献,也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画册印制出来之后,他很开心,抚摸着印制精美的纸张,爱不释手。我知道,他不是贪慕这一点儿虚名,而是觉得这是他风烛残年还能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种见证,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的见证,是他一生奉献、一生付出的见证。他珍视这个荣誉,把画册小心收藏好,不轻易示人。 (下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