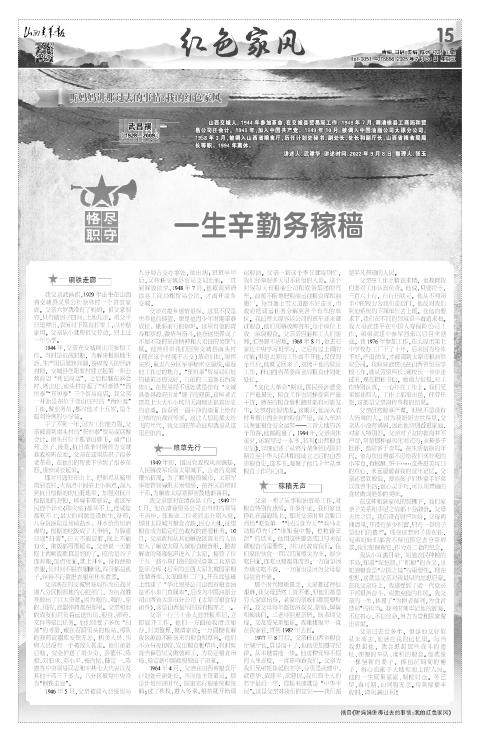一生辛勤务稼穑
武昌祺(1929—2009) 山西交城人。1944年参加革命,在交城县贸易局工作。1948年7月,调清徐县工商局和贸易公司任会计。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被调入中国油脂公司太原分公司。1958年3月,被调入山西省粮食厅,历任计划处秘书、副处长、处长和副厅长,山西省粮食局局长等职。1994年离休。
讲述人:武建华 讲述时间:2022年9月8日 整理人:张玉
钢铁走廊
我父亲武昌祺,1929年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义望公社奈林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六岁就没有了妈妈。祖父家很穷,只有破房子四间、土地几亩。祖父平日里种田,农闲时下煤窑打零工,以补贴家用。父亲从小就帮祖父劳动,只上过一年小学。
1944年,父亲在交城周山庄参加工作。当时是抗战时期,为解决根据地生活、生产用品紧缺问题,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交城县在阳坡村建立起第一所公营商店 “利记商店”,之后相继在麻会村、周山庄、南头村办起了“恒泰昌”“西恒泰”“东恒泰”三个贸易商店。我父亲一开始是在位于周山庄村的 “西恒泰”工作,做业务员,那时他才十五岁,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学徒。
干了不到一年,因为工作能力强,父亲被调到南头村的“东恒泰”贸易商店做会计。南头村位于狐爷山脚下,盛产山药、谷子、莜麦,抗日战争时期曾为交城县政府所在地。父亲在这里结识了很多老革命,在他们的帮助下学到了很多东西,逐步成长起来。
那时日寇驻在山上,把据点从城里筑到农村,大据点中间驻上小据点,深入到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地带,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环境非常恶劣。老区军民连个洋火(即火柴)都买不上,连咸盐都吃不上,最大的问题是没医生、没药,八分区医院是用咸盐水、开水给伤员消毒的。根据地吃饭成了大事情,为躲避日寇“扫荡”,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有火,做饭都得围起来。父亲说一天能吃上两顿饭就算是好的了。吃的是谷子连着糠,加点莜面,就上开水。没有替换衣服,长时间不脱衣服睡觉,浑身都是虱子,痒得不行就把衣服用开水煮煮。
父亲所在的交城贸易局作为抗战时期八分区根据地的心脏部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武器弹药都在那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肩负着运送伤员、粮食、弹药、文件等艰巨任务。他们经受了多次 “扫荡”的考验,藏在石洞里头的粮站、部队的弹药武器库安然无恙,机关人员、伤病人员没有一个被敌人抓走。他们前赴后继,安全护送了刘少奇、彭德怀、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陈赓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共七大代表以及其他干部三千多人,八分区被党中央誉为“钢铁走廊”。
1946年5月,父亲被调入晋绥贸易八分局古交办事处,做出纳;短短半年后,又转任交城县贸易支局出纳。一直到解放前夕,1948年7月,他被调到清徐县工商局和贸易公司,才离开故乡交城。
父亲对故乡感情很深,这里不仅是生养他的摇篮,更是他青少年时期艰难成长、砥砺前行的熔炉。这里有他的青春和梦想、激情与奋斗,他在这里养成了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曾经带我们回到交城县南头村(现在这个村属于古交)革命旧址,缅怀先烈,重走八分区军事秘密交通线,重返他工作过的地方。“东恒泰”贸易局旧址的建筑还算完好,门前的三道条石台阶依旧。在贸易局不远处就是挂有 “交城县委县政府旧址”牌子的建筑,这座老式建筑上大大小小坑凹无言地述说着历史的沧桑。我看到一面干净的墙面上绘有巨幅的抗战宣传画,这让人想起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父亲的革命征程就是从这里启航的。
粮草先行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人民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古老的龙城曙光初现。为了顺利接管城市,太原军事接管领导组未雨绸缪,在各区县培训干部,为解放太原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我父亲那时在清徐县工作。1949年1月,他在清徐贸易公司由当时的领导王吉祥、张振业二位老同志介绍入党。那时太原城内粮食奇缺,民心大乱,征集粮食成为稳定红色政权的首要任务。10月,父亲就和从其他解放区调来的人员加入了解放太原入城粮食接管组,随着解放的隆隆炮声进入了太原,接管了位于五一路小东门街的国民党第二兵站总监部仓库 (后来的山西太原北城国家粮食储备库、太原面粉二厂),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 “华北贸易公司山西省粮食油盐部小东门直属库”,后改为中国油脂公司山西省太原市分公司 (太原市粮食局前身),这是山西最早的国有粮库之一。
父亲一行三十余人进驻粮库后,立即展开工作。他们一方面接收清点库存,归类整理,摸清家底;一方面接收解放区源源不断送来的粮食和草料。他们不分昼夜接收、发出粮食和草料,有时候既当保管员又做装卸工,为稳定粮食市场、稳定新中国政权做出了贡献。
1964年4月,父亲在山西省粮食厅计划处任副处长,当时他主管调运。那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粮油统购统销;过了秋收,进入冬季,粮站就开始调运粮油。父亲一到这个季节就特别忙,我们经常很多天见不到他的人影。这个时候每天有粮油公司和战备集团的汽车,源源不断地把粮油运往粮食库和油脂厂。每当遇上雪天道路不好走时,市政府把调运任务分解到各个有车的单位。我记得太原客运公司的班车还来调过粮食,他们用解放牌客车,每个座位上放一麻袋粮食。父亲亲自指挥工人们装卸,忙得脚不沾地。1969年8月,他去石家庄中央学习班学习,之后有过上调的可能;但是太原的工作离不开他,仅仅四个月后,他就又回来了,继续干他的调运工作,任山西省革委商业局粮食计划处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粮食工作也同样受到严重干扰,潜在的粮食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父亲对此很忧虑。这期间,他深入农村考察山西全省的粮食产量,深入车站以保证粮食安全运转——三晋大地的各个角落,他都跑遍了。1994年,父亲离休前夕,还编写过一本书,名叫《山西粮食史话》,详细记述了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山西省粮食史,这本书,凝聚了他几十年从事粮食工作的心血。
稼穑无声
父亲一辈子从事粮油贸易工作,对粮食特别有感情。许多年前,我们家也挣扎在温饱线上,那时父亲时常会脱口而出“吃饭第一”“民以食为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话来。他用这些警语或口号来强调粮食的重要性,并以此教育我们。我们家的伙食一直以红面擦尖为主,很少吃白面,连吃豆腐都算改善;一方面是因为确实吃不着,一方面也是因为父母提倡俭省朴素。
那个时代物质匮乏,大家都过得很艰难,我父母虽然工资不低,但他们都是穷人家庭出身,老家的亲戚们都需要帮衬。我父母每年都接济叔叔、姑姑、舅舅和姨姨们。二老特别重亲情,既孝顺父母,又友爱兄弟姐妹。我姥姥晚年一直在我家住,直到1987年去世。
1977年8月后,父亲任山西省粮食厅副厅长,算是高干了,但他更加遵守纪律,从未越雷池一步。他这种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们。父亲为我们兄弟姐妹起的名字,分别是武建中、武建华、武建平、武建民,我们四个人的名字最后一字,连起来读就是 “中华平民”。这是父亲对我们的定位——我们都是平凡普通的人民。
父亲在工作上精益求精,他教育我们要对工作认真负责。他说,只要肯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他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我们走后门,他反对我们到他系统的下属单位去上班。在他的要求下,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奋斗着追求着。我大哥武建平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工作,弟弟武建中参军回来以后自主创业。我1976年参加工作,在太原市第七中学校办工厂干了十年,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严重贫血,才被调到太原市粮油供应公司。我妹妹武建民在山西省贸易学校工作,她从劳资科长、副校长一步步走过来,现在担任书记。她能力很强,对工作特别认真,一心扑在工作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工作上都很出色,任劳任怨,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父亲虽然做事严谨,但绝不是没有人情味的人。因为我奶奶去世得早,父亲从小没有妈妈,因此他特别看重家庭,对家人特别好。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并不严苛,常是那种春风化雨式的:表扬多于批评,鼓励多于责骂。在生活拮据的年代,他每次出差都不忘给我们买好吃的小零食,有桃酥、饼干……这些甜美可口的点心,永远温暖着我的童年记忆。父亲还喜欢做饭,爱给孩子们炒拿手好菜以改善生活;他心灵手巧,可以用普通的食材做成绝妙的美味。
在这种和谐家风的照拂下,我们家亲子关系和手足之情都十分融洽。父母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财产纠纷。父母两袖清风,并没有多少积蓄,只有一套房子是他们的遗产。现在这套房子我在住,兄弟姐妹们都舍不得出售它去分割房款,我们想保留它,作为对二老的纪念。
我从小耳濡目染,知道农民种粮的不易,知道“深挖洞、广积粮”的含义,也知道粮食是“立国之基”的重要性。现在想想,这就是父亲对我最早的思想启蒙。在我父亲身上,我感受到了老一代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的作风。我父亲的一生,体现了“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担当。我将时刻牢记他的教诲,不忘初心,不忘使命,努力为党和国家做出贡献。
父亲已去世多年,但是他又好似从未离去,他活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我想起他,就会想起那些战斗的遗址、疾驰的车队、堆积的粮食。他就像一棵坚韧的麦子,捧出沉甸甸的穗子,将心血献于大地和地上的人民。他的一生硕果累累、颗粒归仓。冬已尽,春可期,山河将无恙。待到稼穑丰收时,清风满山冈!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