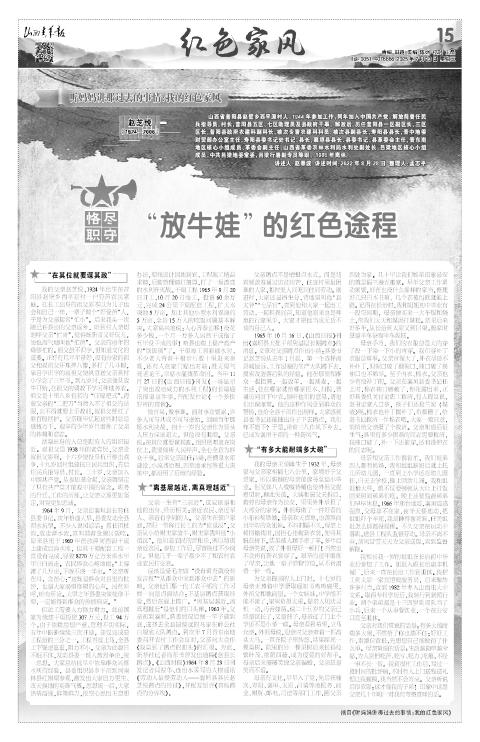“放牛娃”的红色途程
赵芝悦(1924—2006) 山西省昔阳县赵壁乡西平原村人。1944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任民兵指导员,村长,昔阳县五区、七区助理员及县政府干事。解放后,历任昔阳县一区副区长、三区区长,昔阳县政府农建科副科长,榆次专署农建科科员,榆次县副县长,寿阳县县长,晋中地委财贸部办公室主任,寿阳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襄垣县县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晋东南地区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山西省革委农林水利局水利处副处长,吕梁地区核心小组成员,中共吕梁地委常委,吕梁行署副专员等职。1985年离休。
讲述人:赵春波 讲述时间:2022年8月28日 整理人:孟志平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我的父亲赵芝悦,1924年出生在昔阳县赵壁乡西平原村一户穷苦农民家庭。扛长工出身的祖父原本以为儿子也会和自己一样,一辈子做个“好受苦”人,于是为父亲起名“忙小”。后来我头一次随已任县长的父亲返乡,听到村人亲切地呼父亲“忙哥”,觉得既新奇又好玩儿,便也淘气地叫他“忙爸”。父亲的童年的确够忙的。祖父虽不识字,但知道文化的重要。正好有几年年景好,没有分家的祖父和叔祖父汗珠摔八瓣,多打了几斗粮,靠自学识字的叔祖父便执意送父亲到村小学念了三年书。到九岁时,父亲便从放牛开始,在祖父的调教下学习种地务农。祖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 “庄稼把式”,青葱父亲的“二把刀”当然入不了祖父的法眼,由不得就要上手教训,叔祖父便红了脸百般回护。父亲晚年忆起这些时总是感慨万千,艰辛的少年岁月磨炼了父亲的体魄和意志。
贫寒出身的人总是距穷人的组织最近。叔祖父是1938年的老党员,父亲受叔祖父影响,十六岁便投身抗日游击战争,十九岁回村组建抗日民兵组织,先后任民兵指导员、村长。二十岁,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参加革命起,父亲就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职务的升迁、工作的历练,让父亲立场更加坚定,对党更加忠诚。
1964年9月,父亲由襄垣县长转任县委书记。次年恰逢大旱,县委发动全县担水抗旱。不少人说风凉话:抓住担杖钩,放走漳水流,真叫端着金碗讨饭吃。原来县里于1960年在浊漳河西源干流上建成后湾水库,但其干渠配套工程一直没有完成,导致8270万立方米库水年年白白流走。农民群众心疼地说:“上游淹了几万亩,下游不浇一半亩。”父亲听在耳,念在心:“这既是群众对县里的批评,也是大家渴望修渠的心声。民有所呼,咱有所应。大旱之年县委决策续修干渠,一定能得到群众的热情响应。”
但动工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此前国家为续建干渠投资307万元,投工94万个,由于依赖思想严重、管理不切实际,五年中断断续续三次开建,却仅完成总工程量的三分之一。工程再度上马,全县上下疑虑重重,阻力不小。父亲为此数日不眠不休,发动县委一班人激烈争论,统一思想。大家总结抗旱中依靠群众兴修水利的经验,县委组织县乡干部到河南林县红旗渠参观,激发出大家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思想统一后,大家热情高涨,群策群力,挖空心思出主意想办法,渠线设计因地制宜,工程施工精益求精,后勤管理精打细算,打了一场漂亮的水利歼灭战。干渠工程1965年9月20日开工,10月20日竣工,投资60余万元,完成24公里干渠配套工程,扩大水浇地5万亩。加上其他小型水利保浇的5万亩,全县15万人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大家高兴地说:人心齐泰山移!没花多少钱,一个月一万多人居然干成拖了五年没干成的事!咱县也端上稳产高产的“铁饭碗”了。干渠竣工剪彩通水时,不少老人背着干粮步行数十里赶来参观,还有人在家门贴出对联:胜天渠气死老龙王,幸福水灌溉革命田。当年11月27日的《山西日报》刊发《一场显示了突出政治威力的水利工程》的长篇通讯报道这件事,并配发社论《一个多快好省的范例》。
做官易,做事难。面对事功繁累,许多人可与共成不可与虑始。回顾当年那场水利决战,四十一岁的父亲作为领头人压力应该超大,但他没有退缩。父亲说: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组织把咱放在岗位上,就要倾听人民呼声,全心全意为群众干事。后来父亲调任吕梁,在横泉水库建设、小流域治理、四荒地承包等重大决策中,都沿用了后湾的经验。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父亲一生有“三亲近”,这应该是和他的出身、经历相关:亲近农民、亲近军人、亲近有学问的人。父亲生在佃户家庭,昔阳一带称扛长工的为“砍觅汉”,父亲从小给财主家放牛,财主家就叫他“小觅汉”。他知道农民的苦和乐,所以特别亲近农民。参加工作后,尽管换过不少岗位,但他几乎一辈子都少不了和农村农业农民打交道。
应该是受毛主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影响,父亲他们那一代工农干部的工作习惯一向是点面结合:下基层蹲点获取经验,然后在面上推广。“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是他们的口头禅。1963年,父亲初到襄垣,熟悉情况后便一竿子插到底,选择去全县最偏远的马家东岭公社白堰底大队蹲点。到次年7月晋东南地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时,父亲向大会作《我尝到了蹲点的甜头》的汇报。为此,新华社记者冯东书曾发出通稿《赵县长蹲点》。《山西时报》1964年8月29日刊发记者闫振华、连治水采写的人物通讯《劳动人最爱劳动人——襄垣县县长赵芝悦蹲点的经过》,并配发短评《真假蹲点的分界线》。
父亲蹲点不是蜻蜓点水式,而是背着铺盖卷通过访贫问苦,住进村里最困难的人家,和村里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刚进村,大家还显得生分,背地里叫他“县太爷”“七品官”,直到他和大家一起出工劳动,一起担粪间苗,知道他原来也是种地的行家里手,大家才把他当成无话不谈的自己人。
1965年10月16日,《山西日报》刊出《襄垣县大批干部到基层长期蹲点》的消息。文章对父亲蹲点作出小结:县委书记赵芝悦从去年1月起,第一个选择离县城最远、工作最差的生产大队蹲下去,摸索改造落后队的经验。他在那里和群众一起担粪,一起放羊,一起割麦,一起生活,住在哪家就给哪家担水、扫院,普遍访问贫下中农,倾听他们的意见,请他们出谋献策。他的这种作风受到群众的赞扬,也给全县干部作出榜样。大家感到县委书记还能抽出身子下去蹲点,我们咋不能下?于是,带着三八作风下乡去,已成为襄垣干部的一种新风气。
“有多大能耐端多大碗”
我的母亲王荣峰生于1932年,母亲家与父亲家相隔七八公里,家境好于父亲家,所以聪颖的母亲能读书至高小毕业。但兄妹八人嗷嗷待哺也使外祖父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大姨和舅父夭折后,勤劳的母亲作为长女,里里外外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外祖母做了一件好看的小布衫奖励她。母亲欢天喜地,也羡煞尚且年幼的众姐妹。不料时隔不久,母亲上树捋榆钱时,因担心挂破新衣裳,便将其脱在树下。结果被人顺手牵了羊。多年后母亲笑说,挨了外祖母好一顿打!当然也不会再有新衣裳穿了。艰辛的童年锻炼了母亲,让她一辈子惜物节俭,从不肯浪费一针一线。
为父亲提亲的人上门时,十七岁的母亲正捧着中学录取通知书呜呜痛哭,外祖父和她商量,一个女娃娃,中学能不能不读了,家里负担太重。提亲人见状灵机一动,巧舌如簧,说二十五岁的父亲已经是区长了,又是独子,母亲过了门上个学还不是小菜一碟。母亲看到希望,立马允亲。外祖母说,迎亲时父亲牵着一匹高头大马,一直在院子里转悠,结果踩死一棵梨树。院里的另一棵果树后来长得枝繁叶茂、浓荫四蔽,成为度荒的好帮手。母亲后来屡屡笑说父亲骗婚,父亲总是笑而不语。
母亲有文化,早早入了党,先后在榆次、寿阳、襄垣、太原、吕梁等地税务、商业、财贸、邮电、司法等部门工作,随父亲四处为家。几十年让我们姊弟印象最深的就是隔三差五搬家。早年父亲工作调动频繁,好在也没什么像样的家当,整理好几只白木书箱、几个衣被包袱就能上路。记得在长治时,我和姐姐初中毕业有一段空闲期,母亲便买来一大车煤和烧土,带我们天天和煤泥打煤糕。结果后来好多年,从长治到太原又到吕梁,搬家时总是半车杂物半车煤糕。
母亲手巧,我们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改一下染一下小的再穿。我们穿补丁衣服是常事。父亲官做大了,外衣尽量不补补丁,但领口破了翻领口,袖口破了换袖口也不稀罕。至于内衣、棉衣,父亲也少有没补丁的。父亲在襄垣县委书记任上时,棉衣袖口磨破了,棉花露出来,正好县委机关讨论职工救济,有人提议说,赵书记家人口多,孩子们还捡兰炭 (煤渣)呢,棉衣也补丁摞补丁,布都糟了,给赵书记救济一件棉衣吧。大家一致同意,悄悄给父亲报了个救济。父亲知道后很生气:县里有多少困难的同志需要救济,我袖口破了,补一下还能穿,还有没棉衣的同志呢。
母亲和父亲工作都很忙,我们姐弟四人都有奶妈,我和姐姐断奶后就上托儿所幼儿园,一直到上小学还在幼儿园住,白天去学校,晚上回幼儿园。我和姐姐稍大些,就不仅要顿顿从大灶上打饭回来照顾弟弟们吃,晚上还要监督弟弟们早早休息。1966年邢台地震,襄垣震感强烈,父母却不在家,夜半天摇地动,把姐姐吓个半死,我却睡得像死狗,任凭姐姐怎么摇都没摇醒。不久父亲在运动中落职,送县工程队监督劳动。母亲不离不弃,顶风冒雪天天为父亲送饭,直到监督解除。
我和长我一岁的姐姐在长治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姐姐入职长治惠丰机械厂,后来一直在长治工作到退休。我招工到太原一家宾馆做服务员,后来辗转许多行当,直到1982年考入山西电大中文系。取得专科学历后,我转行到新闻行业。两个弟弟都是十三四岁到部队当了小兵,后来一个从事餐饮业,一个在公安口直至退休。
父亲对我们常说的话是:有多大能耐端多大碗,不然给了你也端不住;好好工作,别嫌位置低,先想想自己能做得了什么事。母亲常说的话是:生活越简单越幸福,为人别怕吃苦、吃亏、吃力、吃瘪,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到报社工作后,写过一段时间的批评稿,不时有人上门送钱送礼想让我撤稿,我当然不会答应。父亲听说后很欣慰:这才像我的子弟!印象中这是父亲几十年唯一对我有夸赞意味的话。
摘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