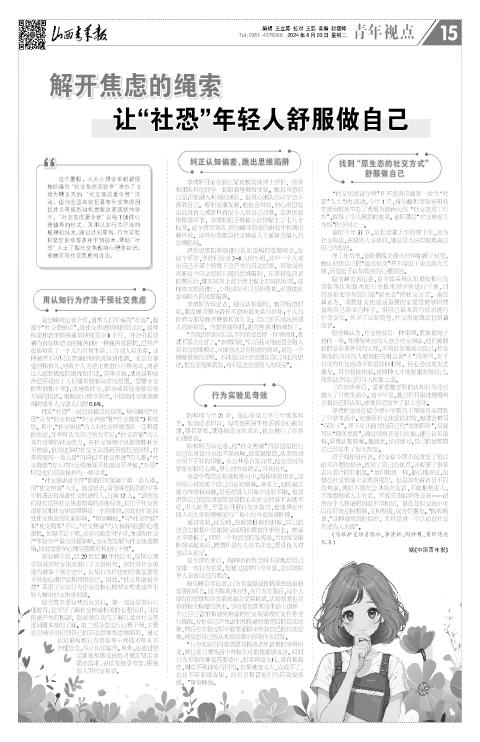解开焦虑的绳索让“社恐”年轻人舒服做自己
这个暑假,人大心理学系副教授唐信峰的“社交焦虑实验室”举办了3场为期3天的“社交焦虑夏令营”活动,面向全国高校招募有社交焦虑困扰并且有强烈动机想要改变现状的学生。“社交焦虑夏令营”以线下团体心理辅导的形式,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的原理和技术,通过认知重构、行为实验和坚定训练等多种干预技术,帮助“社恐”人士了解社交焦虑的心理学知识,掌握应对社交焦虑的方法。
用认知行为疗法干预社交焦虑
唐信峰向记者介绍,通常人们所说的“社恐”,起源于“社交恐怖症”,是社交焦虑障碍的同义词。这种焦虑和害怕情绪通常持续至少6个月,并会引起显著的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指一种痛苦或困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工作或人际关系。这种痛苦不再只是普通的烦恼或情绪低落,而是足够强烈和持久,导致个人无法正常进行日常活动,或者让人感到极度的困扰和不适。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痛苦已经超出了人们通常能够应对的范围,需要专业的帮助和干预),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中国患社交焦虑障碍的成年人占总人口的0.6%。
现在“社恐”一词已经被泛化使用。唐信峰将“社恐”分为“社交焦虑”“社交苦恼”和“社交掩饰”3种类型。其中,“社交焦虑”的人对社交情境感到一定程度的焦虑,并常常认为自己能力不足;“社交苦恼”的人具有足够的社交能力,在社交情境中也能够胜任且不焦虑,但对过多的社交互动感到苦恼甚至厌烦,非常典型的一类人是“内向但不社交焦虑”的人群;“社交掩饰”的人对社交情境既不焦虑也不苦恼,“社恐”只是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话术。
“社交焦虑夏令营”帮助的对象属于第一类人群,即“社交焦虑”人士。通过量表,唐信峰在报名的学生中挑选出有显著社交焦虑的人,每场12人。“虽然他们没有达到社交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但由于社交焦虑症状和社交焦虑障碍是一个连续谱,因此他们也深受社交焦虑的负面影响。”唐信峰说,“与‘社交苦恼’和‘社交掩饰’不同,‘社交焦虑’的人有着明显的心理困扰。如果不去干预,未来可能会对学习、生活和社交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发展为社交焦虑障碍,因此需要在心理学范畴对其进行干预”。
唐信峰介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临床心理学领域对社交焦虑进行了大量研究,在针对社交焦虑的诸多干预方法中,认知行为疗法的疗效显著优于其他心理疗法和药物治疗。因此,“社交焦虑夏令营”采用了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模型来帮助这些年轻人解决社交焦虑问题。
夏令营主要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进行心理教育,让学员了解社交焦虑相关的心理知识,寻找焦虑产生的根源,加深对自我的了解以及对社交焦虑问题本身的了解。第二部分是进行心理干预,主要是引导学员识别自己的自动思维和思维陷阱,通过认知重构和行为实验等干预技术矫正不合理信念,纠正认知偏差。另外,还通过坚定训练帮助成员练习更加坚定地提出需求、表达及接受夸奖、拒绝他人等社交场景。
纠正认知偏差,跳出思维陷阱
李清妍目前在浙江某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经常和团队其他同学一起跟着导师做实验。她很在意自己是否能融入所在的团队,很担心团队的同学会不喜欢自己。哪怕发朋友圈,她也会纠结,担心消息发出后没有人或者只有很少人给自己点赞。在识别思维陷阱环节,李清妍的手臂被小伙伴贴上了七八个标签。夏令营带领者、唐信峰实验室的研究生崔洌川解释说,这些标签都是社交焦虑人士通常会陷入的思维陷阱。
识别思维陷阱是进行认知重构的重要环节,在这个环节,学员们分成2-4人的小组,其中一个人说出自己在某个情境下会产生的自动思维,其他成员判断这个自动思维归属的思维陷阱,在获得发言者的赞同后,就在其身上或手臂上贴上对应的标签。这样依次轮流进行,小组成员可以互相帮助,识别彼此容易陷入的思维陷阱。
李清妍告诉记者,通过认知重构,她开始意识到,朋友圈点赞与否并不意味着关系的好坏;个人的价值与朋友圈点赞数其实无关;自己更不应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当想到这些时,她的焦虑开始减轻了。
“当我意识到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待一件事情时,我就不那么在意了。”李清妍说,“以后我可能还是会陷入原来的思维模式,可能也还会有焦虑的情绪,这是一个慢慢训练的过程。不过我以后会更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想发朋友圈就发,而不是去在意别人的反应”。
行为实验见奇效
陶梓明今年21岁,是山东某大学三年级本科生。他向记者坦言,每次接到陌生电话都会心跳加速,莫名紧张,就连接受这次采访,他也进行了很多心理建设。
陶梓明告诉记者,他“社交焦虑”的原因是担心自己在对话时表达不够流畅,甚至说错话,从而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在公共场合发言时,他也会因为紧张而脸红心跳,担心因为说错话,当众出丑。
在夏令营的认知重构练习中,陶梓明意识到,这些担心其实源于自己的认知偏差。事实上,他的表达能力并没有问题,甚至在别人印象中还很不错。他意识到自己的自动思维是总担心在社交情景下表现不好,引人耻笑,于是在开展行为实验时,他选择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前的广场中间当众做俯卧撑。
通过实验,他发现,在做俯卧撑的时候,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完成俯卧撑这件事情上,焦虑水平降低了。而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当他做完俯卧撑站起来后,周围并没有人在关注他,更没有人对他品头论足。
夏令营结束后,陶梓明仍然会时不时地给自己安排一次行为实验,想通过这种行为实验,尝试向陌生人表达自己的观点。
唐信峰告诉记者,行为实验是最有挑战性也最有效果的环节。因为极具冲击性,在行为实验后,每个人原有的思维和信念系统都会受到挑战,认知偏差也会得到较大程度的纠正。学员要在真实的生活中选择一个让自己害怕和感到焦虑的社交场景或社交任务进行挑战,分析自己产生害怕和焦虑情绪背后的自动思维,然后在实验过程中收集证据来检验自己的自动思维,再反思自己能从实验结果中得到什么启发。
“行为实验的内容需要与挑战者所害怕的事情相关,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有较大可能性能够成功。同时行为实验的难度需要适中,如果难度太低、没有挑战性,则达不到训练的目的。如果难度太大,完成不了,也达不到训练效果,而且会损害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唐信峰说。
找到“原生态的社交方式”舒服做自己
“社交焦虑夏令营”并不是唐信峰第一次为“社恐”人士举办活动,今年1月,唐信峰和实验室研究生皮雨虹还举办了两场为期两天的 “社交焦虑工作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董昕就是“社交焦虑工作坊”的学员之一。
董昕今年31岁,是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生,因为社交焦虑,在跟别人交谈时,她总是无法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工作坊里,董昕胳膊上被小伙伴贴满了标签,她认识到自己的“语无伦次”并不是由于表达能力欠缺,而是出于认知偏差的心理原因。
唐信峰告诉记者,夏令营采用认知重构和行为实验等认知技术和行为技术对学员进行干预,目的是帮助学员回归最“原生态”的社交方式。唐信峰认为,战胜社交焦虑最重要的前提是能够坦然接纳自己原本的样子,用自己最本真的状态进行社会交往。纠正了认知偏差,社交焦虑就会有显著改善。
唐信峰认为,社交焦虑是一种束缚,就像被绳子捆住一样。性格较外向的人也会社交焦虑,他们被捆住的是原本外向的天性,不能自信地展示自己;社交焦虑的内向的人被捆住的则是说“不”的勇气,对于讨厌的社交活动不知道如何拒绝,担心会因此失去朋友。只有驱除焦虑,这两种人才能舒服地做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与人相处之道。
工作坊结束后,董昕把她学到的认知行为疗法融入了日常生活中。这半年里,她日积月累地慢慢纠正着自己的认知,感觉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
李清妍也将在夏令营中学到的干预技巧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中。在感到社交焦虑的时候,她就会填写“应对卡”。在卡片正面写出自己的“思维陷阱”,反面写出“现实思维”,通过将两者进行比较,进行认知重构,调整认知偏差。她感到,经过练习,自己的思维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对于陶梓明而言,社交夏令营不仅改变了他以前不合理的想法,找到了自己的优点,还收获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和我一样,都心地善良,很想在社交情境中表现得更好,但是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焦虑,例如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言,不敢拒绝别人,不敢跟权威人士对话,不敢主动跟异性交流……虽然每个人焦虑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在互相交流中可以很好地互相理解,互相帮助,成为好朋友。”陶梓明说,“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尤其是对一个以前有社交焦虑的人来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李清妍、陶梓明、董昕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